司法实践中,相较于其他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所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简单清晰,举证难度较小,一般仅需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即可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因此,当事人出于简化债权、方便诉讼的目的,常常会选择将因其他法律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转化为借贷关系,并以借条、欠条、借款协议等债权凭证的形式予以重新确认。同时,实践中也时常出现以借贷关系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比如通过虚构借贷掩盖洗钱、诈骗等事实的违法犯罪行为。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对民间借贷案件中基础法律关系审查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文将根据该规定,并结合司法裁判观点,对民间借贷案件中基础法律关系抗辩的裁判规则进行简要梳理。
一、法院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前提条件
诚如上文所言,当事人常常出于各种原因将由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化为借贷关系,并通过内容简明的借据、欠条、借款协议等债权凭证对债权债务进行重新确认。司法实践中,对于原告一方当事人以前述借据、欠条等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主张归还借款,法院应如何审理,存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双方以借据、欠条等形式重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属于自愿将原法律关系转变为借贷关系的行为,法院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仅对借贷关系进行审查,并据此作出裁判。第二种观点认为,由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通常不具备借贷关系的基本要件,尤其不符合实践性合同的特征。因此,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三种观点认为,虽然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但司法裁判应以查明事实为基础,仅对借贷关系进行审查不利于查明债权相关的基本事实。因此,应对原、被告双方的基础法律法律关系所涉事实进行审查,并对基础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认同第三种观点,但是在此观点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即该条款明确规定了法院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前提条件,若要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第二,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第三,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并非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由此可知,在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反诉时,还需进行充分举证以证明案渉纠纷确系其他法律关系引起的。另外,即使符合前述条件,对于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仍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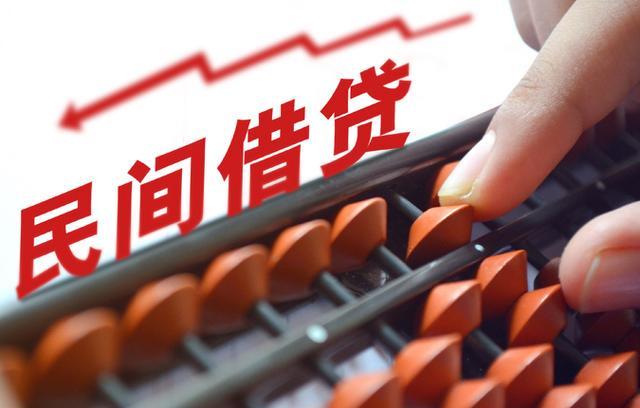
(一)被告未依据基础法律抗辩或反诉,法院不得主动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原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且被告未依据基础法律抗辩或反诉,法院是否可以主动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案件,理论与司法裁判的观点一致,即认为:不得主动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比如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湘10民终1096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根据原审原告胡银春的主张,本案显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审被告刘贤锋、何赛坤答辩时并未以基础法律关系即合伙协议纠纷提出抗辩。且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便刘贤锋、何赛坤以合伙协议纠纷提出抗辩,本案亦属于当事人通过清算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款规定,亦应以民间借贷纠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故一审法院在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主张权利、被告并未以基础法律关系抗辩的情况下,将本案定性为合伙协议纠纷进行审理显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同类型的观点还有(2019)赣0825民初1630号民事判决书、(2019)湘03民终670号民事判决书等。
(二)被告负有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举证责任
由于被告提出基础法律关系抗辩,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故被告需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由民间借贷引起,而是其他法律关系。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终29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本案张德军向爱依公司出具借据,上载明借款金额、借款用途、还款日期、利息标准,张德军签字捺印。爱依公司已向张德军实际支付4000万元借款款项。现爱依公司凭借借据起诉还款,张德军主张案涉款项非借款而系用于抵销张德军对爱依公司的投资款,应当对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苏州市中级法院在(2016)苏05民终6905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三一公司认可收到诉争的80万元款项,但不认可陶情羲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并对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认为双方间系投资关系,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未能使本院对陶情羲所主张的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系由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这一事实产生合理怀疑,故对其抗辩本院碍难采信。”诸如此类的裁判案例还有很多,本文不再赘述。
此类案件中,原告对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一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其证明活动属于本证。被告对于原告的主张进行反驳的证明活动属于反证,其证明标准通常低于本证的证明标准,即其只需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纠纷是否由民间借贷引起这一事实并不确定即可。关于当事人之间基础法律关系性质到底为何,则应由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当然,若被告的举证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则可以直接据此认定基础法律关系。
如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在(2019)苏0804民初708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告李某某所主张的借贷关系事实是否存在,即对《合作协议》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不能排除原告李某某向被告塑胶公司所支付的740万元属于投资款的性质”,本案中,被告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纠纷可能属于投资款争议,使原告主张的借贷关系陷入真伪不明的情形,法院综合案件事实最终认定双方之间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
如苏州市中级法院在(2017)苏05民终7136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由上述聊天记录可见,本案的6万元款项与双方之间的橡胶交易密切相关,黄国永主张本案款项系购买橡胶的预付款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对黄国永的相关辩解予以采信。本案中黄国永虽向钱叶琴出具借条,但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借贷的合意,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借贷关系。”本案中,被告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故而法院认定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借贷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若法院认定当事人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应将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并组织当事人就法律关系性质问题进行充分辩论,而不能简单地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同时,当事人可以根据庭审情况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若当事人未变更诉请,则法院应驳回起诉,不应根据自己的认知径行作出超出当事人诉请的裁判,否则将严重违反处分原则和辩论主义的要求。
(三)审查认定是否属于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对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中所规定的“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具体为何,应进行明确的界定,如此方可判断何种形式的债权债务协议属于该条规定的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第一,所谓调解,在实践中主要有三种:人民调解协议、法院调解协议以及仲裁调解协议。对于法院调解协议和仲裁调解协议,根据《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规定,二者均可以作为执行依据,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无需再提起诉讼处理。对于人民调解协议,通常是指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经过充分地沟通、协调促使当事人之间相互妥协和谅解所达成的协议。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严格遵守协议的约定,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义务。但是,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具备强制性,不能作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当事人因人民调解协议书发生争议的,可以依据协议书达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一经达成调解协议,则应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无需再审查基础法律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除人民调解委员会外,现实中还存在由行业协会、个人或其他主体居中调解促成调解目的,从而形成调解协议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形下所达成调解协议,若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亦应属于通过调解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第二,和解,是指当事人各方之间通过平等协商、沟通,基于互相谅解、妥协就争议纠纷所达成的解决办法,据此形成的和解协议实质上属于契约。根据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时间节点,可以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中和解。诉中和解又可以分为审判阶段的和解,以及执行和解。无论是诉讼外还是诉中达成的和解,均是当事人之间私下形成的解决办法,无需法院出具法律文书,通常由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自行制作和解协议。当事人之间因债权债务问题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相同的是,和解协议也不具备强制性,不能作为执行依据。当事人因和解协议发生争议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处理。此时,当事人基于和解协议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具有约束力,故无需再审查原基础法律关系,法院可依据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裁判。
第三,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对清算的定义为:从广义上讲,是当事人根据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终结法律主体或法律关系,而对业务、财产或者债权债务关系等进行清理、结算以及处分的行为。清算包括对法律主体进行的清算和对法律关系进行的清算,本文所称的清算是指对于某一法律关系而言,即当事人就各方之间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所形成的的权利义务进行的清算。比如买卖合同关系中,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或履行完毕时,买卖双方通过对账、结算等方式就合同权利义务进行清理、处分,确定各自债权债务的行为。此时,买卖双方自愿通过清算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因此无需再审查当事人之间的原基础法律关系,法院可依据债权债务协议进行裁判。
综上所述,无论是调解、和解或清算,均是当事人之间平等协商的行为,由此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均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理论上,符合以上情形的债权债务协议均属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内容。那么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4122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对于《补充协议》签订后的剩余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双方虽在《补充协议》中约定作为青岛交易所的借款,并对利息标准、结息时间等作出约定,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由股权转让关系转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在青岛交易所已经依据基础交易关系即股权转让关系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抗辩,而《补充协议》也并非经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将本案法律关系性质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于法有据。”本案中,当事人已通过《补充协议》约定将争议款项作为借款,并明确约定利息标准、结息时间等,但最高院认为该协议并不属于经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后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6755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关于金星公司与果蔬合作社于2016年6月18日签订《合同书》是否有效,原判决将3278万元认定为借款是否正确问题。根据查明事实,案涉3278万元来源于金星公司与松岚村委于2014年7月26日签订的《东莱街道松岚村旧村改造协议》第九条约定的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资金,后金星公司与果蔬合作社于2016年6月18日签订《合同书》,确认该3278万元欠款的偿还时间、借款期内利息及逾期还款利息,3278万元已经转化为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金星公司与果蔬合作社经过协商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合同书》,属于“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除外情形。原判决将3278万元认定为借款并无不当。”本案中,当事人通过《合同书》约定将争议款项作为借款,并明确约定还款时间、利息等,最高院据此认为该《合同书》属于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对比以上两则判例,我们不难发现,法院对于如何认定是否属于通过调解、和解或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存在不同裁判尺度。尽管如此,本文倾向于认为:对于当事人举证的债权债务协议,如前述判例中的“补充协议”、“合同书”等,法院在审查认定其真实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若该协议系由当事人对已经存在的债权或原债权结算、对账、清算后达成的新的合意,并以借贷的形式予以确认的(如明确约定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时间等),则应认定其属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中所规定的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民间借贷案件,除需审查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外,还需从主体、标的以及内容方面严格审查是否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如审查主体资格、款项交付、资金来源等事实。

二、基础法律关系抗辩引发的管辖权问题
原告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法院在立案过程中将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查管辖问题。鉴于不同法律关系适用的管辖依据可能不同,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基础法律关系管辖与借贷关系管辖不一致的情形,此时被告据此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应该如何审理,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
(一)审查基础法律关系,按照实际法律关系确定管辖
此类观点认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因此,在被告提出基础法律关系抗辩且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应该按照基础法律关系确定管辖。但是,对于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仍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确定管辖。比如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甘民辖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
巩耀文虽以借据、收条为证主张权利,但朱亚东提出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且提交工程协议予以证明,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之规定,本案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应为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合同履行地,巩耀文请求判令朱亚东返还的是其按照合同约定已支付的费用,该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内容应该是朱亚东负有的完成居间劳务的义务,即双方争议标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标的,合同履行地可确定为朱亚东所在地,故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而朱亚东所在地并不在酒泉市肃州区,故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亦无管辖权。据此,本案管辖法院只能依据朱亚东的住所地来确定,因朱亚东为现役军人,隶属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金塔县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较妥。同类型的观点还有(2018)湘10民辖13号民事裁定书、(2020)兵08民辖终36号民事裁定书等。
另外,对于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仍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确定管辖。比如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皖03民辖终40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
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认为本案应按照合伙协议纠纷,其无管辖权。但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因案涉《合作补偿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全面对账结算后签订的,本案不应适用该款的第一条规定。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其无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至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
(二)对基础法律关系不予审查,按照民间借贷关系确定管辖
此类观点认为,案渉基础法律关系为何属于实体审理范围,不在管辖权异议程序的审查范围内,故无论基础法律关系为何种法律关系,均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确定管辖法院。例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8)鄂民辖终38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中民建筑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既提交了2013年1月29日与上诉人鸿丰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建设、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也提供了2016年12月29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和《借据》等证据材料,《借据》上载明借款3200万元,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时据此确定诉讼标的额超过3000万元并无不妥,上诉人鸿丰房地产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中民建筑公司存在可能虚构诉讼标的额起诉的问题,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双方纠纷是否由1200万元工程质量保证金引起,责任方最终承担民事责任总额是否低于3000万元均需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加以判断,属于案件实体审理内容,不属于本案管辖异议审查范围。无论本案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均不影响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地域、级别管辖方面对本案享有的管辖权,故被告鸿丰房地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冀民辖终92号民事裁定书中表达了同类观点:“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基于双方当事人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2016年12月2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而引起的诉讼,尽管借款的由来同被上诉人陈作水与上诉人焦伟之间的投资及清算行为有关,但是否应当依据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属于实体审查的问题。本案应当按照两份借款协议的约定确定管辖。”
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基础法律关系审查属于实体审理的范围,管辖权异议程序中不予审查,应按照民间借贷关系确定管辖。私以为,对于实体审理过程中,发现确应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此时若出现违反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情形,法院可依职权予以移送;对于未违反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情形,但原告在一审辩论终结前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从而导致确定管辖的依据发生变化的,需重新给予被告答辩期,被告有权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应该根据基础法律关系及变更后的诉请确定管辖。

三、总结
民间借贷案件中,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审查基础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明确清楚,对于当事人未提出基础法律关系抗辩的,法院不得主动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提出抗辩的,应充分履行举证义务,否则需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情形,法院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着重审查债权凭证是否系当事人对已经存在的债权或原债权结算、对账、清算后达成新的合意,并以借贷的形式予以确认的情形。
对于因基础法律关系抗辩引起的管辖权问题,应遵循管辖权异议不进行实体审查的原则,按照民间借贷关系确定管辖。若在实体审理中发现确无管辖权的,再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分别处理。
作者简介

冯遵营 资深律师
执业领域为诉讼和仲裁,具备丰富的诉讼实践经验,曾主办过众多疑难、复杂且标的额较大的诉讼案件,负责案件方案的拟定、策划与实施,熟悉法院和仲裁机构的裁判思维和运作方式,能够提供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争议解决方案。
